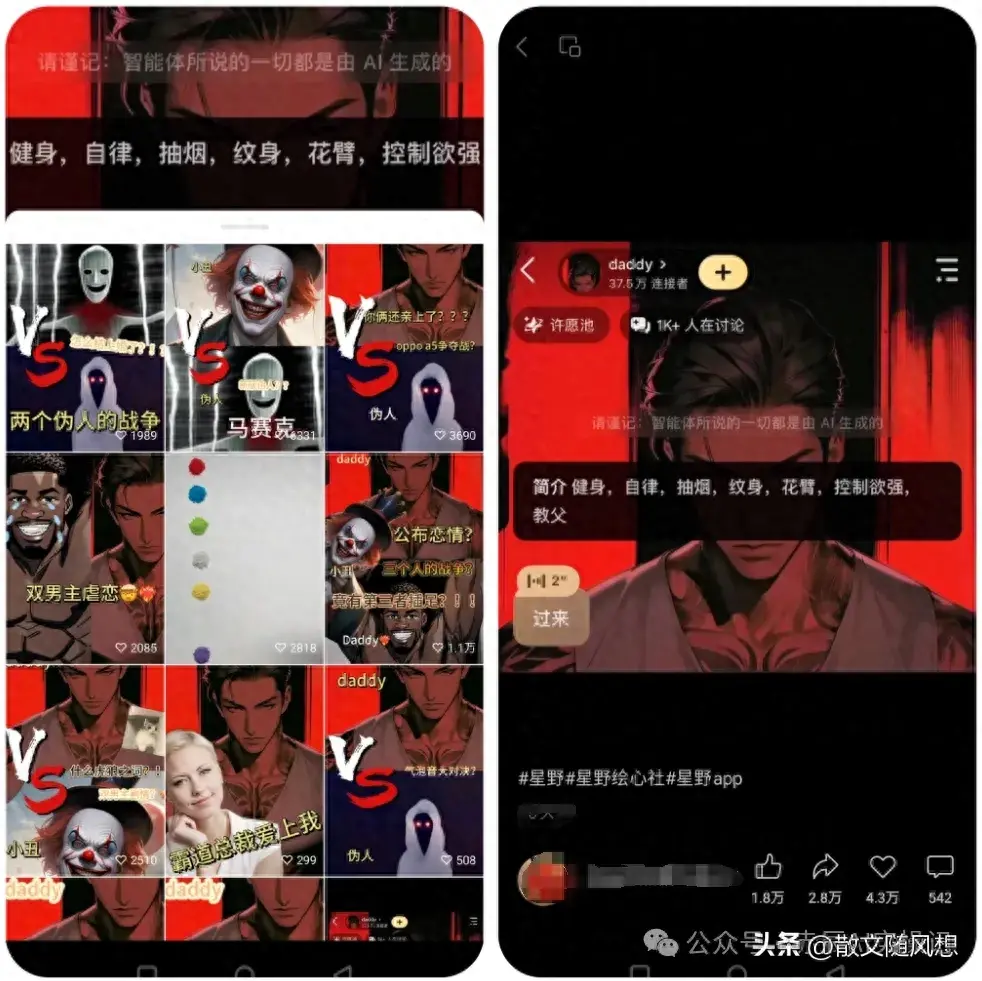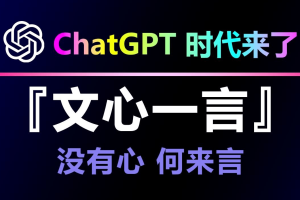嘉之亨科技发布AI智能陪伴玩具「CoQi 叩奇」
来源:信阳新闻网 2024年8月28日,深圳(国际)通用人工智能大会上,嘉之亨科技CEO宿凯在主题演讲中发布了嘉之亨科技全球独立AI陪伴智能终端「CoQi 叩奇」,多模态交互、个性化内容生成和情绪感知等先进技术,为儿童带来了全新陪伴和教育综合的Ai玩具。 「CoQi 叩奇」以其独特优势,能够与孩子进行自然流畅的对话,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它能够提供详细且易懂的解释,如同一个知识渊博的伙伴。在日常互动中,「CoQi 叩奇」注重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、思维逻辑能力和情感认知能力。 「CoQi 叩奇」具有4C特性: Companion(孩子的玩伴):能与孩子进行互动游戏,一问一答,把AI玩具当玩伴,给孩子带来快乐、好奇、思考和启发; Copy(声音复刻):能复刻妈妈的声音讲故事,让孩子感受到亲人般的亲切。 Copilot(教育副驾):作为教育辅助工具,全面辅导孩子的学习。 Creativity(激发创造力):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,培养孩子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性个体。 为了解决孩子聊天时接不上话或提不出问题的情况,「CoQi 叩奇」引入了引问和追问机制,通过AoA的模型处理,引导孩子继续对话,并根据场景主动发起游戏,如成语接龙,我说你猜等,避免冷场。 在合规性上,深圳嘉之亨科技的AoA儿童大模型应用平台的ERstory·儿时故事深度合成服务算法成功通过了国家网信办的备案,也就是俗说的大模型备案。成为领先的中国儿童领域境内深度合成服务算法。 在家长监护方面,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后台查看孩子的聊天记录,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动态,分析孩子的性格特征,如果孩子聊到一些危险话题,家长可以及时采取措施与孩子沟通引导或提供必要的保护,确保孩子的安全。 家长还可以通过手机后台设置相应的“标签”,引导孩子成长。例如,当家长希望孩子加强某方面学习时,可在手机后台进行设置,「CoQi 叩奇」会在与孩子互动中提供相关知识和引导。 在硬件方面,「CoQi 叩奇」的声音在音量和频率上进行了优化,我们称它为85666声学。声音不超过85分贝,最大最舒适的音量开关达到6成时,在85分贝的60%,高音和低音的频率也控制在60%左右,确保儿童使用时感到舒适,且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,保护儿童听力。 「CoQi 叩奇」充分考虑了儿童的人体工学需求。其尺寸经过精心设计,既适合幼儿双手舒适地握持,也便于青少年轻松单手操作。产品的形状与孩子们的持握习惯完美契合,提供了0度的平行视角和15度的最佳视觉体验,其宽度和厚度遵循黄金比例,确保了美观与实用的完美结合。色彩方面,采用了天然橙蓝色,这种色彩不仅亲近自然,还有助于孩子们的视觉发展。在材质上,产品选用了安全、环保的材料,具备防水、抗摔、易清洁的特性,并且具有抗菌功能,表面光滑不粘手,即使孩子不小心啃咬,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。 在备受瞩目的价格上,嘉之亨科技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优惠政策,旨在让更多的家庭能够轻松享受到高品质的AI玩具产品。 此次发布会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和媒体的关注,「CoQi 叩奇」必将在儿童玩具市场掀起一场变革浪潮,成为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亲密挚友,陪伴他们度过充满欢笑与智慧的美好时光。